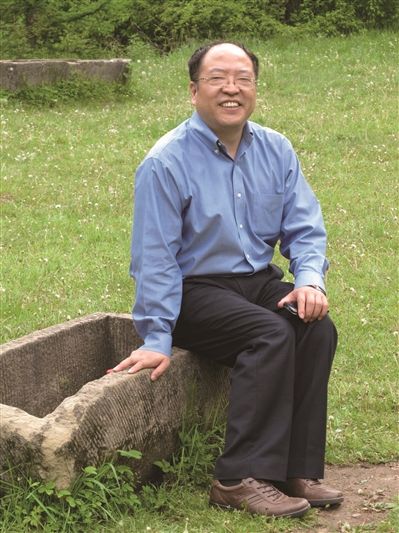
雷雨
最早知道陳老蓮,是看到他的關于水滸的插圖,實在是太令人喜愛了。但給世人的印象,為小說刻本畫插圖,似乎并非大畫家所為,陳老蓮也許潦倒困頓,迫于生計,畫些插圖,只是為稻粱謀?不是說,以晚明遺民自居的陳老蓮不懂經營拙于生計嗎?他放浪形骸,茍活于亂世,也僅僅是為了活命,在寺廟里呆過一年,紅塵中的綽約女子,他怎能舍得?有人甚至說,只要有女人,陳老蓮都會慨然應允,為之作畫。清人毛奇齡《陳老蓮別傳》里說,1646年夏天,陳洪綬在浙東被清軍所擄,“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而陳老蓮的好朋友張岱則稱其為“字畫知己”。陳老蓮,字章侯,出生于諸暨望族,張岱系紹興名門之后,一方水土所孕的奇才異趣,再加兩人年齡又相去不遠,早年一同讀書于“岣嶁山房”,后又多次一同出行訪友。《陶庵夢憶》所記“甲戌十月”,兩人和眾友人一起到不系園看紅葉,陳洪綬“攜縑素為純卿畫古佛”,并“唱村落小歌”,張岱則“取琴和之,牙牙如語”,如此瀟灑疏狂,無拘無束,宗子感懷舊事,怎不感懷唏噓?張岱在其《石匱書》中把陳洪綬列于“妙藝列傳”,稱他“筆下奇崛遒勁,直追古人”;陳洪綬眼中的張宗子則是“才大氣剛,志遠博學,不肯俯首牅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閑置……”,言語間皆是高山流水惺惺相惜。張岱說,雖然陳老蓮的畫名在生前就已得到承認,“然其為人佻傝,不事生產”,以至順治九年暴斃時竟至無以成殮,時年陳老蓮也才54歲啊。張、陳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在大清,一個“披發入山”,一個“剃發披緇”,在心態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遺民,張岱記錄陳洪綬的四句自題小像:“浪得虛名,窮鬼見誚,國亡不死,不忠不孝”,語間全是明末清初文人的大痛楚。據說,甲申之變的消息傳來時,陳洪綬正寓居于徐渭的青藤書屋,悲痛欲絕之下,他“時而吞聲哭泣,時而縱酒狂呼,見者咸指為狂士,綬亦自以為狂士焉。”《陶庵夢憶》還記述了陳老蓮有一次喝高了去追一陌生女郎的風雅趣事。1639年,時近中秋,張、陳二人在西湖邊的畫舫遇一女郎宣稱要搭船同游,此女“輕紈淡弱、婉瘞可人”,本來喝得昏昏欲睡的陳洪綬頓時興奮莫名,兩眼炯炯,他以唐代傳奇中的虬髯客自命,要求與此女同飲。女郎竟然也毫不扭捏作態,落落大方,欣然就飲,把船上帶的酒都給喝空了。老蓮仗著酒意朦朧,醉問女郎家住何處。女郎總是笑而不答,巧做掩飾。等她下了船,陳洪綬在后面暗暗跟蹤,只見此女倩影飄過岳王墳,就杳如黃鶴。也許在三百多年前的舊時月色下,陳洪綬真是遇到此后蒲松齡筆下的狐貍精了。
看不少人談到陳老蓮,都會提到所謂“南陳北崔”之說,但這個說法究竟來自何人?崔子忠到底有何種成就?卻語焉未詳。眾所周知,陳老蓮與張岱是至交摯友,來往多多,但張宗子并無此論。“四十年來誰不朽,北有崔青蚓,南有陳章侯。”卻原來是吳梅村題《凌煙閣功臣圖》詩中的句子,這其中的陳章侯就是陳洪綬,時與北京崔子忠被并稱為“南陳北崔”。吳梅村也是明清易代之際的大文人大名士,其心境情緒自然與陳老蓮有息息相通之處。陶元藻《越畫見聞》中記載:陳洪綬“生平喜為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為搦筆也。”陳洪綬在浙東被清兵所俘,清兵以刀脅迫其作畫,他卻“力拒不允”,誠如后人評論陳老蓮:“后來海上四任學他,即便得其‘清圓細勁,森森然如折鐵紋’的特點,得其怪誕之姿,卻畫不出他的苦澀,他的人生況味真的都入了畫中”。
1998年,是戊戌變法百年紀念。在常熟,遇到了翁同龢的后人翁萬戈先生,此人很是精明博學,他在美國建有自己的莊園萊溪居,言語間,他很是看重自己陳洪綬研究專家的頭銜。翁同龢父子喜歡陳老蓮的畫,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薪火相傳,文脈有續,翁萬戈也成為陳老蓮研究專家,倒是一樁佳話了。后來,津門劉岳先生,曾贈送翁萬戈主編的《陳洪綬畫集》,瞻顧再三,令人流連。翁同龢在其詩文中至少有六次提到陳老蓮,采擷摘錄一二,與大家分享,也說明,此說不虛。
在《翁同龢詩集》瓶廬詩稿卷四中,翁同龢題陳章侯畫博古牌刻本冊為黃小松故物。戊子正月收得之。長嘯江潭有餓夫,低顏來對牧豖奴。不知十萬腰纏客,可抵三酸博士圖。桑孔區區言利臣,陶朱猗頓善謀身。可憐寒乞書生腹,公輩能容數百人。翁同龢所說的戊子正月,即1888年正月。黃小松,即黃易(1744 —1802), 字大易,號小松、秋盦,又號秋影庵主、散花灘人,浙人。在《翁同龢詩集》瓶廬詩稿卷五中,翁同龢這樣寫道:重題章侯畫博古牌刻本次前韻, 己丑二月九日,得章侯為豫和尚畫八枼,喜而賦此:
突兀蕭疏有此夫,瑯華二水總書奴。云寒雪薄春風厲,忽憶吾家三友圖。(章侯《歲寒三友》卷,先公所賞,今在南中。)吳山道觀有遺臣,白發黃冠畫里身。忘事已多翻閱懶,不知老豫是何人?翁同龢說的章侯就是陳老蓮,先公自然是指他的父親大學士翁心存了。翁同龢在《三題章侯畫博古牌刻本次前韻》中也感慨道:文學何須笑大夫,上林古有牧羊奴。要知商戰今宜講,能得斯才亦本圖。愧我硁硁作計臣,曾無膏澤及民身。楚茶折閱吳棉戝,愁煞東南數郡人。
翁同龢在《題陳章侯三友圖》前的按語說:此《三友圖》,道光己酉,先公得之于吾邑沈氏,喜誦其詩,常以自隨。先公既卒,吾五兄攜之入湘、入鄂。去年吾省墓歸,又攜以北。每一展卷,不覺涕泗之橫集也。庚寅長至前一日,齋宮侍班歸,檢視此卷,因題一詩,后人能謹護之否?玄冬動琯灰,云物謁皇州……
翁同龢說到的五兄,即翁同爵,曾任湖北巡撫、署理湖廣總督。翁同龢“后人能謹護之否”之句,可見陳章侯“三友圖”于翁氏家族之意義所在,翁同龢于詩中明確表明“我于近人畫,最愛陳章侯”,于翁同龢言,前朝畫家中,最愛當數沈周,而以其之時代作為觀照的近人畫家中,最為傾賞的則是陳洪綬。從“衣縚帶勁氣”到“逸氣真旁流”,算是翁同龢對陳老蓮作品的鑒賞品讀,語重心長,發自肺腑,堪為知音。歲月無情,人世滄桑,翁萬戈面對先輩“后人能謹護之否”的疑問,當會有非常人所能體悟的感受吧。
《翁同龢詩集》瓶廬詩稿卷五中,又有松禪老人“元夕題陳章侯畫博古牌刻本次前韻”:劉毅輸錢亦壯夫,朱三睨視豈狂奴?……
在《翁同龢詩集》瓶廬詩稿卷六中,翁同龢說:偶見陳章侯畫水滸枼子疊前題博古牌冊韻。丁酉十月三日,園居臥疾,有攜書畫來者,章侯畫《水滸》小冊甚妙,即此冊跋語所謂“《水滸》枼子”也。開闔數次,不能釋手,是日仁壽殿演禮,臣龢在賜酒之例,退而賦此。
一笑探囊慰老夫,那堪庸史與書奴。陳生妙具屠龍手,卻寫江湖伏莽圖。親酌天漿賜近臣,自驚衰鬢久忘身。陳生餓死臣溫飽,一樣疏狂淡蕩人。
《翁同龢詩集》瓶廬詩稿卷六,還有翁同龢《題陳老蓮橅古冊》。 己亥,二冊共二十枼,為林仲青作,先五兄所收以畀余者也。己亥三月,墓盧展玩,因憶所見悔遲諸跡,輒題四詩:
最好金陵剪雨圖,夜堂捧硯有吳姝……
突兀俄驚丈六身,嬋娟不耐作天神……
竹平安館舊裝池,仿佛西園李伯時……
眉舞軒中孰雁行?仲青仲豫兩詩狂……
翁同龢家族顯赫宦海沉浮,雖然其晚景凄涼,困守家園,其政治遭際與張宗子也大相徑庭,但兩人殊途同歸,都鐘愛陳老蓮的畫作,激賞陳老蓮的藝術,這樣的審美趨同,難道與他們的家世相關?陳老蓮喜歡畫怪石、芭蕉,喜歡畫枯藤老樹,喜歡在人物頭上插畫,尤其是男人,給人以怪異非常之感。陳老蓮說,千年壽藤,覆彼草廬,其花四照,貝錦不如。有客止我,中流一壺。浣花溪人,古人先我。正是江南仲春時節,在古拙虬枝上,又有姹紫嫣紅的小花淺斟慢酌,次第開放,在陳老蓮看來,這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是對暗淡人世間的一種一年一度的撫慰,青山不老,綠水長流,春來草自綠,秋去江水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這樣亙古如斯,我們何必去蠅營狗茍,還是如《小窗幽記》中所說的那樣去自我陶醉吧:
凈一室,置一幾,陳幾種快意書,放一本舊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揮塵,意思小倦,暫休竹榻。餉時而起,則啜苦茗,信手寫《漢書》幾行,隨意觀古畫數幅。心目間覺灑空靈,面上塵當亦撲去三寸。



已有0人發表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