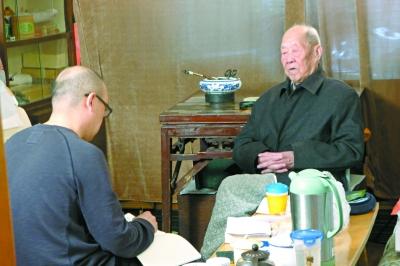
“太原會戰(zhàn)”攝制組采訪抗戰(zhàn)老兵周錫奎。
記者 周南焱
一個團,一千多人戰(zhàn)死,從團長到士兵,幾乎全部犧牲……然而,這場70多年前發(fā)生在山西繁峙縣鷂子澗村的慘烈戰(zhàn)斗,在史書上卻只有四個字:全團陣亡。
壯懷激烈的戰(zhàn)斗,輕描淡寫的文字,橫跨兩者之間的是一段塵封的歷史。
歷史紀錄片《共赴國難——太原會戰(zhàn)》,試圖用鏡頭還原諸如此類的被忽略的抗戰(zhàn)史。該片由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攜手太原市委宣傳部攝制,通過重走太原會戰(zhàn)的戰(zhàn)場遺址,采訪健在的抗戰(zhàn)老兵,呈現(xiàn)鮮為人知的抗戰(zhàn)史細節(jié),比如,遲到的血色紀念碑。
抗戰(zhàn)老兵的心愿
千人團犧牲77年后才立碑
雖說此前曾看過有關(guān)太原會戰(zhàn)數(shù)十萬字的史料,但紀錄片首席記者郭曉明、編導楊程等人,不想把《共赴國難——太原會戰(zhàn)》拍成一部史料宣傳片。怎么拍?一度令人撓頭。
直到今年4月中旬,太原關(guān)愛抗戰(zhàn)老兵志愿者打來電話,說他們計劃重走太原會戰(zhàn)的北線戰(zhàn)場遺址。聞此,郭曉明、楊程不由眼前一亮,當即決定同行。
攝制組和志愿者從太原出發(fā),驅(qū)車300公里,第一站到達山西北部繁峙縣鷂子澗村。
這個村位于山澗之中,四圍傍山,偏僻孤靜。戰(zhàn)爭的硝煙早已散去,如今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大多都不知道在這片土地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
1937年8月,國民革命軍第72師434團在鷂子澗遭日軍包圍,程繼賢團長及官兵1000余名,全部陣亡。這段歷史,史料無具體記載。
去年初,志愿者曾看望年過九旬的太原抗戰(zhàn)老兵周錫奎,他是434團目前唯一健在的老兵。多年來,老人心底藏著一個愿望:當年自己的團長、戰(zhàn)友都戰(zhàn)死在鷂子澗村,想讓志愿者過去看看,在那里為戰(zhàn)友們立一塊碑。不久之后的4月份,志愿者完成了老人的心愿,在鷂子澗村后的山坡上立起一塊遲到的石碑,并在碑旁四周圈出一個石臺,種上樹木,形成一個小小的烈士陵園。
攝制組和志愿者特意來到碑前獻花。緬懷過后,攝制組人員拿鐵鍬在一個疑似墓堆的地方,挖了1米多深,挖出一些骨頭,但并不能確定是否為犧牲將士的遺骸。村子里已無絲毫戰(zhàn)爭遺跡,唯一了解當年戰(zhàn)斗犧牲情況的一位老人,當年只有9歲,他并不知道烈士的遺骸葬在何處。
“站在碑前,我們心里的感受很復雜。”楊程唏噓不已,“78年前的那場慘烈戰(zhàn)斗,現(xiàn)在只有一塊碑作為見證。這個村子人跡罕至,成了被人遺忘的地方。”
日本軍官的敬意
特意為中國陣亡軍隊立碑
在太原會戰(zhàn)的忻口戰(zhàn)役中,原平縣曾是第一道防線。在這里,攝制組的鏡頭偶然拍到一座“中國無名戰(zhàn)士慰靈塔”,確切說只是殘存的“碑塊”。
孤零零地,這座塔碑被置于縣城的一個廣場上,平時無人注目。令人大感意外的是,立碑者竟是一名日本人——日軍柳下部隊的軍官大田雄太郎。據(jù)說這座塔碑是前幾年在原平縣的一個龍王廟里被發(fā)現(xiàn)的,之后才挪到了這個廣場上。此前,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也可謂是一塊遲到的紀念碑。
查閱大量中日史料之后,郭曉明發(fā)現(xiàn)這可能是日軍在中國大陸唯一為一支中國陣亡軍隊設(shè)立的慰靈塔。大田雄太郎所在部隊,當年跟國民革命軍196旅作戰(zhàn)。1939年大田雄太郎再次回到原平,特意為中國軍人立了這座慰靈塔,碑上寫著“為永久追悼在原平戰(zhàn)爭中戰(zhàn)死的4300名無名戰(zhàn)士亡靈設(shè)立慰靈塔”——正面是中文,背面是日文。
因為此前做過《我的抗戰(zhàn)》系列紀錄片,楊程從抗戰(zhàn)老兵的口述中聽說過196旅死守原平的事跡:旅長姜玉貞撤退時被日本人的炮火擊中,一個日本軍官竟殘忍地把姜玉貞的頭顱割下……196旅5000人,最后只剩700人——在軍史專家看來,原平保衛(wèi)戰(zhàn)是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初期,華北地區(qū)較慘烈的一次戰(zhàn)役。
“原平離忻口只有20公里,不過是一座孤城,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中國軍隊硬是堅守了10天,給忻口決戰(zhàn)布防留下了時間。”楊程說,就連日軍都覺得不可思議。為了表示對中國軍隊的敬重,大田雄太郎才會立碑紀念中國陣亡軍隊。
臺灣上將的緬懷
熱血將領(lǐng)陣亡處題字立碑
在忻口戰(zhàn)役遺址,攝制組發(fā)現(xiàn)了另一塊紀念碑,同樣令人意外。
1937年10月,在忻口會戰(zhàn)中,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在前線督戰(zhàn)時不幸中彈,在倒下后仍高呼殺敵報國,壯烈犧牲,年僅39歲。郝夢齡是抗戰(zhàn)期間中國軍隊犧牲的第一位將軍。
依據(jù)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編輯的《我的抗戰(zhàn)2》所述,忻口戰(zhàn)役前夕,郝夢齡曾給妻子寫信:“此次抗戰(zhàn),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后關(guān)頭,抱定犧牲決心,不成功即成仁……余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為國家戰(zhàn)亡,死可謂得其所矣!”
如今,郝夢齡犧牲的地方,遺跡全無,只有一個光禿禿的山包,其后面則是連綿的山峰。距離郝夢齡陣亡地不到5公里的一條山溝,是他當年指揮作戰(zhàn)的指揮所,如今這里已然荒蕪,但幾十口窯洞依然保存完好,見證著當年戰(zhàn)爭的血與火。
去年,臺灣原“行政院長”郝柏村到訪大陸,特意來到郝夢齡陣亡處,發(fā)現(xiàn)那里竟然連一塊碑石都沒有,倍感遺憾。原來,郝柏村也是抗戰(zhàn)老兵,后任臺灣當局一級上將,生平對郝夢齡欽佩有加。太原關(guān)愛抗戰(zhàn)老兵志愿者隨即請郝柏村為郝夢齡事跡題字。拿到字之后,他們立即尋找石材,鐫刻字跡。今年4月,紀念碑順利落成。
立于碑前,攝制組和志愿者莊重敬獻鮮花。“作為一名指揮官,郝夢齡完全可以藏在指揮所里,但他挺身奔赴戰(zhàn)斗最前沿,真的令人充滿敬意。”楊程說。
崢嶸歲月,煙山火海,一代將領(lǐng),凜然之氣長存!
回望
他們記憶中的戰(zhàn)斗
在緊張的拍攝結(jié)束后,攝制組與志愿者協(xié)商,找到了四位健在的太原抗戰(zhàn)老兵,做口述史采訪。
這些老兵都已年過九旬,包括老兵周錫奎、閻錫山警衛(wèi)連戰(zhàn)士許有德、1936年參加犧盟會的老兵崔文煥和晉綏軍炮兵趙子星。郭曉明說,這些老兵的身體還好,記憶大多很清晰,但畢竟年紀大了,一個上午也就聊一個多小時。從老兵們的口中,攝制組聽到不少戰(zhàn)爭細節(jié)。
對周錫奎來說,1937年繁峙縣鷂子澗村的那場戰(zhàn)斗,是埋在他心底幾十年的痛。
當時,周錫奎是一名搜索兵。他說,自己能活下來是一個奇跡。他記得,那天團長程繼賢帶主力在村中休整,遭到日軍反撲包圍。而他所在的連,在村外警戒,看到團部被包圍就趕回來增援。連長派了三名搜索兵在前邊走,其中就有周錫奎。他們往前走,中了日軍的埋伏,機槍一響,身邊的兩個戰(zhàn)友全犧牲了。知道日軍火力點的具體位置后,連長派一個排往前沖,結(jié)果沒幾分鐘全排人都被日軍機槍打死了;第二個排沖,打死了;第三個排再沖,又打死了……就這樣,一個連的兵力全部犧牲。而周錫奎因為在完成任務(wù)后一直隱蔽在溝里,直到戰(zhàn)斗結(jié)束后才出來,所以幸免于難。
郭曉明還采訪了八路軍的一名老衛(wèi)生員朱維漢,據(jù)其回憶,在平型關(guān)戰(zhàn)役中,686團副團長楊勇負傷,衛(wèi)生員幫楊勇包扎好腿之后,和楊勇的警衛(wèi)員一起趴在地上,楊勇趴在他們的背上,他們就用手扒地匍匐前進,楊勇也在兩個人的背上用手扒地……撤下戰(zhàn)場后,三個人手上全是血。在朱維漢看來,現(xiàn)在的抗戰(zhàn)劇中,陣地上架起傷員就撤離的情節(jié)完全是瞎扯,實際上日軍的子彈到處飛,架起來跑早被打死了。
老兵們的戰(zhàn)爭回憶,說起來還有太多太多……
雖然郭曉明曾看過很多抗戰(zhàn)史料,但老兵們的口述讓他感觸更深,“看書有時一眼就過去了,不會有太多感覺。而聽了老人的回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戰(zhàn)爭的血腥與殘酷。”他說,接下來,攝制組計劃去山西采訪一些老八路軍。
尋訪之路,沒有盡頭。
補白
太原會戰(zhàn)
發(fā)生于1937年的太原會戰(zhàn),以太原為中心,包括天鎮(zhèn)戰(zhàn)役、平型關(guān)戰(zhàn)役、忻口戰(zhàn)役、娘子關(guān)戰(zhàn)役和太原保衛(wèi)戰(zhàn)。這是抗戰(zhàn)初期華北戰(zhàn)場規(guī)模最大、戰(zhàn)斗最激烈、持續(xù)時間最長、戰(zhàn)績最顯著的會戰(zhàn)之一,前后歷時兩個月,斃傷日軍3萬余人,是國共合作抗日配合最好的一次會戰(zhàn)。
紀錄片預計9月央視播出
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計劃做“抗戰(zhàn)之城”系列紀錄片,依托跟抗戰(zhàn)有關(guān)的各個城市來講述抗戰(zhàn)史,重走抗戰(zhàn)遺跡。攝制紀錄片需要資金,目前答應合作的只有太原市政府,于是《共赴國難——太原會戰(zhàn)》成為此系列的第一部紀錄片。該片將口述歷史、外景拍攝、檔案資料三者結(jié)合,分為上下集,單集時長30分鐘,計劃于今年9月在央視播出。
文章來源:北京日報 責任編輯:劉姍(實習)


已有0人發(fā)表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