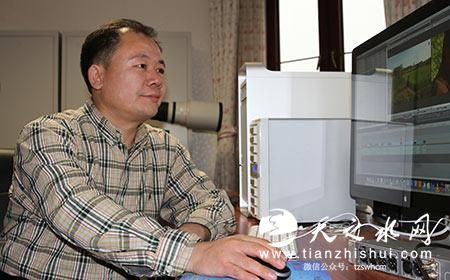
2015年6月9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小說月報》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揭曉,旅居天津的天水籍作家秦嶺的短篇小說《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榜上有名,這是秦嶺繼中篇小說《皇糧》獲得原創百花獎以來,再次榮獲以“百花”命名的全國性獎項。獲獎作家還有鐵凝、賈平凹、蘇童、遲子建、趙玫、方方、畢飛宇、葉廣芩、嚴歌苓等。
《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以西部干旱地區為背景,描寫了一位懷孕的女人和同樣懷孕的狐貍用生命的挽歌捍衛尊嚴、彰顯靈魂、呼喚大愛的故事。小說一經《人民文學》雜志發表,即以獨特的視角和普世價值引起文壇廣泛關注,被許多大學搬上課堂,同時登上中國小說學會2014年中國小說排行榜,納入中國現代文學館《當代文學經典必讀》(短篇卷)等多種選本。據悉,本屆評獎共評出包括長、中、短篇小說獎,小說雙年獎,小說新人獎,散文獎和散文特別獎等7個獎項。評選活動由讀者和專家共同參與,并將于6月25日至28日首次以“走紅地毯”方式舉行頒獎活動。
秦嶺曾就讀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系活躍于全國文壇一線的青年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小說集《皇糧鐘》、《借命時代的家鄉》、《殺威棒》等10部,主編文集20余種,小說40多次入選各類權威選本選刊,散文曾入選《五年制小學語文實驗課本》和全國高中聯考、高考模擬試卷。長篇文學作品曾兩次被納入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短篇小說3次登上中國小說排行榜,獲各類獎項10多次,參與主創的影視、戲劇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特等獎等,曾被天津市宣傳文化系統評為“五個一批”優秀人才,也是天津市唯一被中國文聯授予優秀個人稱號的青年小說家。
把內心照亮
——訪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得主秦嶺
【摘要】在我看來,優秀的文學必然布滿了社會的神經。社會越是無序和喧囂,文壇越應該清醒和警覺,這一點,我非常看好西方文學家的思想和姿態。而我們不少人面對文學卻是輕佻的。
問:短篇小說《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榮登2014年中國小說排行榜,入選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等多種年度選本,這次又榮獲第16屆百花獎,您認為這部作品為什么如此受歡迎?
秦嶺:小說一經《人民文學》發表,我即感受到了來自專家、讀者的青睞和熱情。您一定注意到,很多評論中都提到喚醒、永恒、普世等令人欷歔的字眼,我自己也深受感染。今年“讀書節”前后,一些高校邀請我講座的緣由,多與生命的尊嚴、大愛的尋覓、生態的呼喚、人性的反思、價值的判斷等人文元素有關,我想,這也許是來自女人和狐貍生命的呼喚吧。有學者說:“把我們的內心照亮”。這一定是讀者歡迎它的理由。
問:《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的畫面感非常強,文字所要展現的畫面感和影視劇的畫面感有沒有區別?所謂“畫面感強”的文學作品是否在改編影視作品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秦嶺:您提到的畫面感,實際上是中外小說創作中最為寶貴的審美品質之一,其主要特征是細節和描寫。在過于偏重形式和技術的當下,許多人有意繞開這一鐵門檻,而我選擇跨過去。在我看來,只有畫面意象才能彌補女人、狐貍兩個不同物種的行為交流和心理博弈。文字展現的畫面感與影視劇的畫面感既有區別,也有聯系,二者表現人物行為層面的“畫面”優勢永遠無法相互替代,但心理層面的“畫面”,文字與影像的抵達始終是一致的。畫面感強的文學作品改編影視固然得天獨厚,但前提是小說“畫面”轉換之后,必須滿足影視“畫面”的指向,也就是區別之外有聯系的部分。
問:報刊和網上有很多賞析《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的文章,作者有專業評論家,也有文學愛好者,其中不少分析得十分細致,讓人想起學生時代做閱讀理解題時老師的講解。您更希望人們以怎樣的心態和方式欣賞您的作品?
秦嶺:這一現象既鼓勵了我,也讓我警惕,當這篇小說和之前的《棄嬰》、《殺威棒》、《摸蛋的男孩》被一些大學、中學教師從國情教育角度搬進課堂時,我真正體味到當年章德寧、楊顯惠諸賢提出的“秦嶺的小說提供了認識價值”的深意。當下中國的現實為作家提供了非常豐厚的思考養料,考驗作家的除了技術的智慧,重要的是觀察、思考與判斷社會的硬功夫。在重力加速度的時代,我們不該讓現實瞬間變成歷史的廢墟,我愿意我的讀者保持一種冷靜和從容感受我的小說,因為我所有的質疑、追問和批判,都把歷史和現實納入當下來判斷。我閱讀別人曾屢屢上當,我不能讓讀者上我的當。
問:《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與您之前的《皇糧》《在水一方》等不同體裁的作品,創作思路有哪些聯系和區別?
秦嶺:聯系在于都是反映社會變革時代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心靈世界,區別在于體裁、表現方法的路徑不同。《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用了現實加魔幻的手法,以“水”為背景,把人與獸類放在同等的、公平的靈魂天平上,考量生命和精神的尊嚴。而長篇《在水一方》是紀實的,為了反映飲水安全這一全球關注的嚴酷現實,我斗膽融入了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的技法,我相信寫實的沖擊力,同時也相信虛構超越真實的可能性。嘗試的結果是,這部書被納入中國水文化研究的重點圖書。值得一提的是,《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借命時代的家鄉》、《被馬咬掉耳朵的主人》等中短篇,均與我關注飲水民生有關。我和央視主持人朱軍對話的主題是《水是舉頭三尺的神明》,是水、神明這樣的字眼帶給我內心的震撼,加速了我在紀實、虛構、想象之間的不斷變換。“皇糧”系列包括《皇糧鐘》、《皇糧》、《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小說,題材因素,我用了寫實之法,在我看來,沒有任何文學的母體能夠像綿延達2600多年的皇糧史足以反映農民內心的隱痛了。“民以食為天,食以水為先。”人,一要喝水,二要吃飯,連我自己都沒料到,我的文字會落到老百姓的杯子、飯碗里。
問:在《皇糧》創作談中,您曾提到該系列改編的電影、電視和戲劇,大概只有農民才會感興趣,那直到現在為什么還在堅持寫農村題材,對城市讀者的信心有沒有增長呢?
秦嶺:記得那個創作談的題目叫《有一種蒙昧我不愿相信》,也是我6年前榮獲第十三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的感言。當那么多城市居民享受城鄉“剪刀差”的巨大紅利而對中國農民付出的慘重代價不明就里時,當寧可享受低保而不愿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下崗職工對建設現代都市的農民工嗤之以鼻時,這種糟糕的文化心理足以讓全人類驚詫和質疑。根據“皇糧”系列改編的多個劇種吸引了很多農村觀眾,也摘取了很多大獎,但它打動城市觀眾很難,其中包括象牙塔里的某些知識分子,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盲流”、“閑散人員”、“城市不穩定因素”、“待遣返人員”等概念,就是知識分子的可恥發明。我之所以選擇面對鄉村,是因為農民經受的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折磨讓我欲罷不能,而籠罩城市居民心頭的多是精神的迷茫,這種迷茫其實更為悲哀,它與無情、自我和欲望有關。我的許多小說其實是把城鄉融為一體的,城市,其實是鄉村的鏡子。我對城市讀者當然充滿期待,我今后寫城市的時候,必然會把鏡子掉過來。
問:農村缺水、上繳皇糧,都是當代城市人不太熟悉的元素,您是否將這種“喚醒”視為自己的一種責任?
秦嶺:責任這個詞,在我看來是很恐懼的。我寧可認為,寫水、寫糧食是我的宿命。三年前,水利部從中國作協推薦的十多名作家中,最終選擇委托我行走鄉村考察飲水狀況,開始我并沒答應,但我突然就想到了故鄉甘肅大地灣出土的史前時代先民們用來取水的尖底兒陶罐,想到了我兒時在山洼里擔水、在枯井邊等水的記憶。同樣,我有過早在八九歲時就背著小麥、拎著籃子給城里人上繳“皇糧”、鮮蛋的經歷。當這些記憶與現實的都市鏈接,眼前仿佛有一個巨大的黑洞,走出這個黑洞的唯一路徑,就是創作了。當我回味從維熙、蔣子龍等方家以“歷史的刻度”定義我的創作時,我也感受到了“喚醒”的力量,在一次政協會議上,有好幾個“富婆”委員告訴我,看了《女人和狐貍的一個上午》,再也不忍心穿皮草了,再也不敢浪費一滴水了,愿意把洗衣服的水節約下來沖馬桶。有些單位在民生教育中還以“皇糧”系列為例,宣講人與糧食之間最基本的關系。
問:您曾經提到希望人們能用歷史、社會、生命、宗教的視角審視文學,這對小說來說要求是否太高了呢?尤其是在關注度原本就被其他藝術形式分散的當下。
秦嶺:在我看來,優秀的文學必然布滿了社會的神經。社會越是無序和喧囂,文壇越應該清醒和警覺,這一點,我非常看好西方文學家的思想和姿態。而我們不少人面對文學卻是輕佻的。譬如,很多文學評論家習慣于就文學論文學,習慣了在形式上兜圈子,很少有人跳出文學本身,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觀照文學;成為作家的門檻也很低,個人情緒的宣泄、人性惡俗的刨挖很容易以文學的名義被津津樂道。這樣的東西,疑似批判現實的,實質上是迎合世俗和俗世的。正如建筑大師們在京城創造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專業人士陶醉其中,卻絲毫不顧民族、社會的審美理想與文化水土的歷史適應性,文學存在同樣的幽默,這也是它在藝術形式分散的當下不夠強勢的原因之一。我這樣講,不是有意抬高文學的標桿,而是在此岸遙望文學的真容。
問:如今人們閱讀的介質逐漸向移動化、電子化演變,作為文學創作者是否要順應這種變化,比如在作品結構、篇幅和題材等方面。
秦嶺:新媒體時代,變與不變同樣會有市場。不久前,天津外國語大學的一位教授邀請我為其小說作序,打動我的是她筆下文學與網絡聯姻之后的開闊性,是把故事框架敲碎以后用圖片影像代替文字的觀賞性,是英、漢雙語交替敘事的文化共融性,是電子光盤語音輔助詮釋的立體性、詩性和神秘性。小說之所以在大陸和英語國家受到歡迎,是因為她在高雅與流行中靠近了受眾的審美之根。我欣賞這種探索與創新的科學性,但我自己的創作肯定要背對這種范式的,我也在顛覆自己,但那是堅守中的顛覆和顛覆中的堅守,這與我的審美與路數有關。(據網絡 作者系百花文藝出版社編輯)【原文作者:胡曉宜】



已有0人發表了評論
您需要登錄后才可以評論,登錄| 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