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biāo)題:蘭州羊皮筏子,抗戰(zhàn)中運送物資的“軍艦”

美國記者卡爾和雪萊夫婦于1941年在蘭州黃河邊拍攝的蘭州筏客。

1941年,美國記者卡爾和雪萊夫婦于蘭州拍攝的筏客子們在捆扎羊皮筏子的情景。圖片除署名外均為首席記者 王文元 翻拍

黃河蘭州段上載客的筏客子,美國記者卡爾和雪萊夫婦攝于194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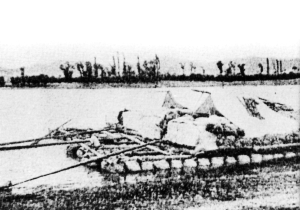
黃河蘭州段裝滿貨物待發(fā)的羊皮筏子。

黃河上的羊皮筏子。首席記者 裴強 攝
匯集皮筏成立“水上運輸隊”
1942年夏的一天,嘉陵江重慶段的水面上一只奇特的漂浮物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線中。它既不是木質(zhì)輪船,也不是鋼制艦艇,而是由金黃色氣囊托浮著柵板組成的船形物,上面整齊地排放著許多油桶似的貨物。“一只,兩只,三只……”這只奇特的船隊慢慢停泊在化龍橋碼頭。有人高喊:“羊皮筏子,這是羊皮筏子!”人們這才知道,這就是傳聞中的由油礦局雇傭從廣元向重慶運送汽油的皮筏。
碼頭上擠滿了為燃油所困的接貨人員,他們顧不得日機隨時前來轟炸的危險,擁向碼頭,去接收貨物。面對迎接的人群,二十名憨厚樸實的筏客把目光齊刷刷投向一位漢子。這位漢子就是這次筏運的領(lǐng)頭人、蘭州水上運輸隊業(yè)務(wù)負(fù)責(zé)人王信臣。
此刻,他像往常一樣,正在從容地指揮筏客們卸貨,與前來接貨的貨主進(jìn)行交割。而一年前的一幕,卻又重現(xiàn)在他眼前。
那是1941年夏,國民黨政府油礦局總經(jīng)理孫越崎專程趕到蘭州,與有關(guān)方面洽談從嘉陵江中下游用蘭州皮筏向重慶運輸汽油。通過當(dāng)時的蘭州市政府同意,孫越崎找到筏戶王信臣,讓他試辦此事。
早在1939年,蘭州的筏戶們就曾向靖遠(yuǎn)共產(chǎn)黨組織運送過物資。1940年,當(dāng)時的甘肅省政府成立了驛運管理處,將蘭州所有皮筏編為“水上運輸隊”,王信臣是筏上業(yè)務(wù)負(fù)責(zé)人。運輸隊的主要任務(wù),就是將槍彈、汽油等軍運品,運送給寧夏的馬鴻逵、馬鴻賓和綏遠(yuǎn)陜壩一帶的傅作義部隊。
現(xiàn)在,向重慶運送汽油,作為蘭州水上運輸隊的筏上業(yè)務(wù)負(fù)責(zé)人,王信臣知道,嘉陵江雖然上游河內(nèi)礁石險灘星羅棋布,但中下游卻河面寬廣,水深流緩,適宜皮筏航行。然而,問題不在水上,而在空中。他最擔(dān)心的是日機的轟炸。幾年來,他親歷了日機對蘭州的轟炸,耳聞目睹了市民遭受到的傷亡。他推測,作為陪都的重慶,遭到日本侵略者飛機的轟炸程度一定會比蘭州更加嚴(yán)重得多。
重慶當(dāng)時的實際情形正如王信臣所推測的那樣。抗戰(zhàn)之初,日本侵略者飛機就對重慶進(jìn)行了多次轟炸。特別是1939年5月3-4日的“重慶大轟炸”,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大慘案。這兩天,日機共7批63架次空襲重慶,炸死3991人,傷2323人,毀房4871間。1941年夏,日本飛機更是變本加厲,對重慶進(jìn)行“疲勞式轟炸”。日軍在這一階段異常猖狂,轟炸機經(jīng)常單獨進(jìn)攻,并在行動半徑極限值附近進(jìn)行轟炸。這樣一來,嘉陵江航道自然也成為日機轟炸和襲擾的目標(biāo)之一。
試航成功蘭州筏客運送汽油300噸
經(jīng)考慮再三,王信臣提出先由自己親自試航一次,沒有危險再航運。孫越崎同意了。
王信臣挑選了2名筏工,在孫越崎的安排下,到了廣元,用孫越崎從蘭州購買的400個皮胎扎成了一個皮筏,裝載了1000多公升汽油,啟程試航。雖然不知面臨日機轟炸,筏工們?nèi)绾纹丛诩瘟杲系那榫埃嚭降慕Y(jié)果是王信臣成功地抵達(dá)了目的地。
試航成功后,王信臣增加了信心。他答應(yīng)了孫越崎的要求。翌年夏,他挑選了20多名筏工,成立了“皮筏航運隊”,赴廣元執(zhí)行運送軍用物資的任務(wù)。他們用油礦局從蘭州購買的2000多個羊皮胎,扎制了5只巨型皮筏,每只能夠載重60噸,共裝載了300噸汽油,開始了前途未卜的軍運航行。
從廣元到重慶的直線距離是700公里,但由于重慶部分河段的曲折蜿蜒,實際航程將超過1000公里;再加上五只皮筏同時航行,目標(biāo)大易暴露,若遇日本飛機轟炸,不容易躲避。這意味著他們的航期將比預(yù)定的要長,所冒的風(fēng)險也將很大。因此,這次航行,要比試航更難,更要精心籌劃,保證萬無一失。據(jù)史料確鑿記載,經(jīng)過了15天的艱難航行,王信臣率領(lǐng)的筏隊終于抵達(dá)了重慶。
皮筏在嘉陵江上航運成功轟動了山城。油礦局舉行了盛大的“歡迎皮筏航運隊大會”,新聞單位攝制了電影紀(jì)錄片。
羊皮筏子真正成為具有軍用功能但不用燃料驅(qū)動的特殊“軍艦”,據(jù)說,“羊皮筏子賽軍艦”一句民謠,就是從那時候流傳下來的。一直到1943年,運送汽油一年多之久的皮筏運輸隊完成了運輸任務(wù),返回了蘭州。
(本文刊發(fā)時,編輯有刪改和調(diào)整)
作者:魏宏舉甘肅省檔案局
“筏客子”,烽火中的水運兵
古有詩云,黃河“河流迅且濁,湯湯不可陵。”生活在河兩岸的古老先民們,用樸素的智慧制造出了“羊皮筏子”,劈開這湯湯之水,遨游其上,便捷實用;
1941年,當(dāng)時的國民黨政府組織蘭州的30名筏工來到四川、重慶運送軍用物資,“羊皮筏子賽軍艦”的美譽就此傳遍大江南北;
一位筏工于8年前去世,他的子孫們,現(xiàn)在依然在黃河里撐著羊皮筏子,曾經(jīng)的戰(zhàn)火硝煙,只為了今天這般美好的時光,不負(fù)當(dāng)初,守望生活。
黃河上千年皮筏劈浪開
作為最原始的運輸工具,羊皮筏子已經(jīng)在黃河上漂流了千余年,古稱“革船”,古人“縫革為囊”,充入空氣,泅渡用。到了宋代,皮囊是宰殺牛、羊后掏空內(nèi)臟的完整皮張,不再是縫合而成,故名曰“渾脫”,渾做“全”,脫即剝皮。《宋史王延德傳》也有“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于水”的記載。
據(jù)說,從前最大的羊皮筏子有500只羊皮囊,能載重幾十噸,串聯(lián)起來的羊皮筏子大如巨舟,在滔滔黃河上漂行,氣勢壯觀。一段關(guān)于羊皮筏子的順口溜流傳至今:“躥死一只羊,剝下一張皮,捂掉一身毛,刷上一層油,暴曬一個月,吹上一口氣,綁成一排排,可賽洋軍艦,漂他幾十年,逍遙似神仙。”寥寥數(shù)語,概括了羊皮筏子的制作流程。
甘肅的皮筏大多都是羊皮制成,劃筏子的人被稱作“筏客子”,多是黃河兩岸的回族人。擺渡時皮筏順流而下,返回時,則由筏客子扛在肩膀上,步行到上游,故有“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之說。
1919年,甘肅第一位走向新生活的新女性代表鄧春蘭,就是乘坐羊皮筏子從蘭州白馬浪渡口順流而下去的北京。她在旅行記中寫道:“經(jīng)鹽場堡、十八家灘,而入桑園峽。水勢峻險,波濤怒號,令人驚懼欲絕。入大峽,水勢愈覺可悚。動心駭目,不可注視……”
1930年前后,蘭州共有蘭州幫、靖遠(yuǎn)幫、青城幫筏戶三幫,共有羊皮筏子百余只,從事一些短途的客貨運輸。隨著羊皮筏子駕駛技術(shù)的改進(jìn),1932年以后,蘭州到包頭的水上航運業(yè)務(wù)就全由羊皮筏子擔(dān)任了。
那些身懷絕技的人們,把囫圇扒下的羊皮吹成大皮囊,綁在木條上,推下河岸,便成了與浪起舞的小舟。黃河浪上,一葉看似晃悠悠的羊皮筏子起伏飄蕩,筏客子們邊靈巧地劃動邊唱著古老的花兒:“我黃河上度過了一輩子,一呀輩子,浪尖上我就耍花子;我雙手嘛就搖起槳桿子,槳呀桿子,好像是天空里的鷂子……”
抗戰(zhàn)中頭頂烽火穿急流
63歲的張德寶是筏子世家,他爺爺曾看守過黃河鎮(zhèn)遠(yuǎn)浮橋,父親張為民也當(dāng)了一輩子的筏客子,在老戶口簿上,父親的職業(yè)是“皮筏工人”。過去,黃河上除了鐵橋再少有直通道,過河的人大多乘筏子,羊皮筏子除了為過河的人擺渡外,更多的是貨運。
張德寶祖輩們常給人運木材、羊毛、販鹽。而不為人知的是,他的父親曾在抗戰(zhàn)時期到過四川、重慶,參與過“皮筏航運隊”,為當(dāng)時的國民黨政府運送過抗戰(zhàn)物資。這段歷史,張德寶的父親在生前很少提及,直到10多年前,有位記者來家中采訪羊皮筏子的故事時,父親才提起自己曾去過重慶,運送過軍用物資。
1941年,國民黨政府的油礦局總經(jīng)理孫越琦來到蘭州,想用筏子試辦從廣元到重慶1400多華里的運輸業(yè)務(wù)。他購買了羊皮囊2000個,編成5個大皮筏,聘用筏客子20多人,成立了“皮筏行運隊”,次年夏天,當(dāng)筏子隊歷經(jīng)15天(木船需一個月)到達(dá)重慶時,轟動了整個山城。
張德寶說,一般而言,羊皮筏子都是由13個羊皮囊串成的,中間5個,前后各4個,能坐六七個人。而用2000個羊皮囊編成5個大皮筏,每個皮筏用囊400個,密密麻麻排在木排上,足有現(xiàn)在常見到的羊皮筏子的30個大,5個同時漂在江面上,何其壯觀。再用這5個羊皮筏子載300噸汽油,一路蜿蜒漂流1000公里,其中的艱難險阻,可想而知。
對于這些,他的老父親絕口不提,后輩們鮮有知曉。1944年,這位老筏客子給國民黨某部隊運送汽油時,7個押解士兵被水卷走,他漂了一里地后才爬上岸。1948年,筏隊再次遇險,張為民眼睜睜地看著岳父被湍流淌走,自己卻無能為力。
隨著蘭州地區(qū)道路、橋梁的增多,陸路交通的改善,黃河上游水庫的興建和大型鋼船的不斷投入使用,黃河上游的皮筏運輸業(yè)才日漸蕭條。1968年,張為民終于收起了經(jīng)營了大半輩子的羊皮筏子。但他將制作羊皮筏子、劃筏子的技藝傳給了兒孫們,直到2007年去世,活了近90歲。
現(xiàn)如今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上世紀(jì)60年代,十一二歲的張德寶就開始放筏子。改革開放后旅游趨熱,張德寶抓住機會,成了最早在黃河上經(jīng)營筏子的人之一。經(jīng)過幾年發(fā)展,他和內(nèi)侄成立了蘭州宏達(dá)旅游服務(wù)有限公司,目前已成為蘭州黃河邊上最大的羊皮筏子經(jīng)營公司。張德寶說,實際上,筏子要比快艇安全,快艇一翻就沉,筏子即使翻了,人只要抓住上面的木桿子,就不會有危險。
每年從春暖花開到秋葉飄羅,張德寶每天都在黃河上劃筏子、開汽艇。筏子從黃河母親漂流到中山橋附近,再由汽艇運送游客和筏子返回。到冬天時,他又開始制作筏子,去年一個冬天,他就做了300只皮筏。“前幾年會做皮筏的人少,現(xiàn)在慢慢多了,我們公司20來個人都基本上學(xué)會了。”制作羊皮筏子的手藝很復(fù)雜,從選皮、浸料、扎制都有講究,他都教給了自己的后輩和員工們。
近年來,隨著媒體的不斷報道,張德寶家的羊皮筏子聲名遠(yuǎn)揚,一些人除了大老遠(yuǎn)趕來觀賞和游覽外,每年還有美國、日本、港澳臺的客人專程來購買羊皮筏子。
去年,火爆一時的《爸爸去哪兒》來到了景泰黃河石林邊的龍灣村,爸爸和萌娃們體驗了一把黃河漂流,也讓更多的人知道了羊皮筏子,許多游客慕名前來乘坐。張德寶說,自己雖然已經(jīng)63歲了,但覺得身體還行,還能趁著好機會多干幾年。實際上,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從前,由于經(jīng)常浸泡在水中拉筏子,他的雙腿關(guān)節(jié)活動不太靈便,蹲下再站起來有點費勁,走路也斜著。一雙手粗糙、寬大,骨節(jié)已經(jīng)有點變形,黝黑的紋路暗藏著歲月的磨礪。
滔滔黃河中,筏子踏浪而去。當(dāng)年水運隊的老兵已被長河淹沒。硝煙已成記憶,歲月依然靜好。
記者 魏娟
文章來源:中國甘肅網(wǎng)-蘭州晨報 責(zé)任編輯:劉姍(實習(xí))


已有0人發(fā)表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