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小說第六部《偷窺者》出版,接受新京報專訪,笑稱網(wǎng)劇、電影主演都是照著他選的
法醫(yī)秦明:寫作只是愛好,不會干涉影視版
小說《偷窺者》中加大了對幾位主人公感情線的描寫。在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秦明笑言,盡管自己是海巖的“鐵粉”,“從小到大”看著海巖的作品長大,但自己還是沒有學到海巖的精華,不擅長描寫人物愛情,“這是我最弱的一項,想嘗試慢慢加一點進去,寫到后面就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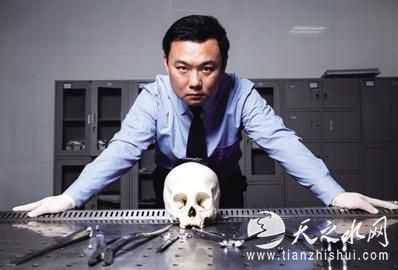
去年,改編自小說《第十一根手指》的網(wǎng)劇《法醫(yī)秦明》創(chuàng)造了16億的點擊量,原著作者秦明也打響了知名度。今年8月,他帶來了“法醫(yī)秦明”系列小說的第六部《偷窺者》,從一樁樁少女失蹤事件開始,展開十個彼此獨立的離奇兇案,法醫(yī)秦明與伙伴們一同尋找潛藏在幕后的偷窺者。
秦明就職于安徽省公安廳物證鑒定中心,2012年,第一部“法醫(yī)秦明”系列小說《尸語者》出版后紅遍網(wǎng)絡。從此,他走上了“作家”之路,以他和周邊同事經(jīng)歷的親身案例,為讀者講述法醫(yī)是如何通過現(xiàn)場勘查、尸體檢驗來進行現(xiàn)場分析、重建,從而破獲疑難案件的。
而改編自《尸語者》的電影版《生死語者·秦明》日前也已殺青,秦明本人還在片中客串了一個“小角色”。采訪中他也分享了一個拍攝中的花絮,化妝的時候,秦明說:“老師,你能幫我化帥一點嗎?”愣了三秒以后,化妝師說:“我不干了!”
作為目前刑偵探案劇的大IP作者,秦明坦言,自己并非影視行業(yè)的人,不會對拍攝進行干預,但通過他的作品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法醫(yī)這個行業(yè),讓他非常自豪,“包括一些同事的孩子會說,一部好看的劇讓他們對父母的工作產(chǎn)生自豪感,我覺得特別欣慰。”
選擇入行
做法醫(yī),為的是爸媽都滿意
2005年,秦明獲得醫(yī)學和法學雙學士學位,考入安徽省公安廳正式成為一名法醫(yī)。
高中畢業(yè)后,當秦明考入皖南醫(yī)學院時才發(fā)現(xiàn),全班40個人,只有他一個人第一志愿填了法醫(yī)。那時候法醫(yī)還很冷門,全國只有20個法醫(yī)專業(yè)的畢業(yè)生。他記得大一時,高中同學帶著朋友來,第一次見面的人聽說他學法醫(yī),不愿意和他握手。“到我大二那年,隨著港劇《鑒證實錄》《法證先鋒》和美劇《CSI》風靡,大家對法醫(yī)才從歧視和畏懼轉(zhuǎn)變?yōu)檠瞿胶秃闷妗!倍赃x擇法醫(yī)這門學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爸爸是個刑警,媽媽是個護士,兩個人都想讓兒子繼承自己的事業(yè)。為了讓爹娘都滿意,秦明想干脆學“法醫(yī)”,將刑偵和醫(yī)學融合在一起。
秦明從小就很崇拜當警察的爸爸,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他還透露了一個“小秘密”,“就悄悄跟你講,其實我悄摸兒地在提前錄取的志愿里面填了一個人民公安大學偵查系。后來因為視力不行,被刷掉了,所以入行學了法醫(yī)。”爸爸在秦明眼中一直非常偉岸,“他是搞痕檢(痕跡檢查)的,就是檢查指紋、腳印,一個命案現(xiàn)場就法醫(yī)、痕檢兩個專業(y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跟我爸經(jīng)常開玩笑,說我們倆可以出一個命案現(xiàn)場。”
以至于在秦明開始工作之后,還會把自己的案子拿給爸爸看,聽取他的意見,“他也會給我一些提示。他說哎你看,這個柜門上的血跡就說明了,殺人的時候柜門是開著的。我就會推導出這是一個盜竊轉(zhuǎn)化為搶劫的案件,一個小的推理就可以決定一個案件的性質(zhì)。”
法醫(yī)工作
辛苦之外,剛?cè)胄袝r總被歧視
法醫(yī)的實際工作遠不如在《鑒證實錄》中聶寶言那般的英姿颯爽,既要參與重大疑難命案的現(xiàn)場勘查、尸體檢驗、現(xiàn)場重建分析,還要做死因和傷情復核鑒定、信訪案件的處理工作等。在網(wǎng)劇版《法醫(yī)秦明》中,秦明和林濤、大寶為了尋找尸塊,在漆黑腐臭的下水道中“摸底滾爬”,很多網(wǎng)友吐槽電視劇中的道具和場景太過逼真,其實這都是秦明的真實工作狀態(tài)。
“觀眾只是視覺上的沖擊,而現(xiàn)實中的法醫(yī),還要承受觸覺、嗅覺上的沖擊。”首先,尸臭就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秦明的妻子是小他兩屆的法醫(yī)系學妹,就是因為忍受不了這種味道,一畢業(yè)就轉(zhuǎn)了行。“尸臭太難聞了,而且黏附力極強。這些氣味分子很多脂溶性良好,容易沾染在人的體表、毛發(fā)甚至毛孔,很難去除。尸臭不僅刺激耳鼻,也會污染衣服,法醫(yī)們通常都是自己洗衣服,不讓家人觸碰。有時候進一次解剖室,出來后洗三天的手,味道都還在。如果沾染了特別濃烈的尸臭,有的法醫(yī)只好在值班室躲兩天再回家。”
剛?cè)胄袝r,秦明覺得戴兩層手套活動不便只戴一層,工作結束后,因為手上的味道,兩天沒有吃飯。經(jīng)前輩支招,從此秦明兜里常裝一把香菜,出門見人,都先用香菜搓搓手改改氣味。“有人吐槽香菜是最難吃的東西,沒有之一,但在我們法醫(yī)眼里,香菜是最好用的東西,沒有之一。”
法醫(yī)這些鮮為人知的艱苦經(jīng)歷都是秦明寫書的原因。“我剛?cè)胄械臅r候是覺得我們這個職業(yè)是遭受很多歧視的。有人會不愿意跟你握手、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吃飯。還有人認為法醫(yī)代表著死亡,法醫(yī)去給傷者驗傷的時候,傷者就會很抵觸,說我不就受傷嘛,你法醫(yī)來干嗎呀!”
故事創(chuàng)作
取材真實,但會尊重被害人家屬
秦明的小說有一個特點,所有故事都是從真實案件中取材,“故事會做藝術加工,但案件細節(jié)全是真實的。”他還試圖在書中普及一些法醫(yī)學知識,諸如尸斑是怎么形成的,鈍挫傷的刀口是什么樣的,如何利用尸塊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等等。在秦明看來,任何一個法醫(yī),都必須是“尸語者”——能聽懂尸體語言的人,“眼睛看到的不一定真實,只有用手術刀才能解讀死者最后的語言。”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紀律”,“公安涉密手段是不能寫的。還有就是在寫作的過程中不能侵犯當事人的利益,不能讓那些被害人的家屬一眼就能看出來,你是在寫我家的事。這樣的話,你會對他又是一種刺激,這個也是我需要去避免的。”
于是,創(chuàng)作時就必然要改編。一開始的改編可能比較簡單,把案件換一個背景、換個人數(shù)、換個作案的方法就改編了。秦明說,現(xiàn)在改編會更精致一些,“我平時在偵案的過程中,從A推導到B,我會把這個推理過程記在本子上,時間一長,就會記錄幾十條、幾百條這樣的推理細節(jié)。在寫作的時候,在這里面選取一部分,把幾個細節(jié)組合成一個案件。”
秦明說,寫書之后,賺的錢是比以前多了,但比起自己的法醫(yī)職業(yè),寫作永遠是他的業(yè)余愛好。
“我寫書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法醫(yī),讓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法醫(yī)隊伍。可只要是工作時間,我是決不會分心考慮其他事情的。”
【對話秦明】
干到退休的法醫(yī)對這份職業(yè)都充滿了熱愛
關于影視版
新京報:“法醫(yī)秦明”網(wǎng)劇和電影版的主演張若昀和嚴屹寬都是高顏值演員,劇組定演員的時候,會征求你的意見嗎?
秦明:定演員不就是照著我定的嘛(笑)。我也不會太去干涉。每個行業(yè)有它自己的規(guī)則和道理,有它的理論所在,我是個外行人,不懂(影視)。而且我相信合作方一定在找演員的時候,會選擇最合適的。事實證明也是這樣,我認識的演員們都非常刻苦認真,對法醫(yī)這個職業(yè)有很深的理解。這個我是完全放心的。
新京報:現(xiàn)在《法醫(yī)秦明》算是大IP作品了,影視化的過程中,你會有參與嗎?
秦明:娛樂圈的事情我也不會去涉足。要說一定涉足的話,我就是在這些劇、電影里面擔任總編劇或者總顧問,會對其中一些不合常識或者寫得比較飄兒的東西進行修改。然后和演員交流,培訓一下器械怎么拿,以及(解剖)手法,會讓他們做得更逼真。
工作危險性
新京報:現(xiàn)實的法醫(yī)在工作中會遇到什么樣的危險?
秦明:法醫(yī)犧牲的人數(shù)可能沒有緝毒警察那樣多,但是現(xiàn)場的不定性因素都會威脅到法醫(yī)的安全。比如1991年,我就有個師兄在勘察爆炸案的現(xiàn)場犧牲了。毒氣、爆炸物,這些東西是你不可預估的,犯罪分子有可能潛伏在現(xiàn)場,你也不知道。我有個老師,在進下水道的時候,全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中毒會瞬間失去意識,他就掉下去了。幸虧有人給他弄上來了,要不然也很危險。這樣的風險是來源于現(xiàn)場,也有來源于尸體的,你并不知道他有什么艾滋病、乙肝這些烈性傳染病。在解剖的時候,弄破了自己手都會很緊張。
近年,我們也開始注重法醫(yī)的自我防護了。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有些縣是買不起一次性手術衣的,他們會用白大褂,洗完了再穿。你可以想象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現(xiàn)在一次性手術衣已經(jīng)都能滿足了。
法醫(yī)的困惑
新京報:法醫(yī)在整個公安系統(tǒng)里的地位還是比較低?
秦明:在我國,法醫(yī)就是警察的一分子。但法醫(yī)畢竟是幕后工作者,雖然不能說地位低,但在功勞簿上比較難看見。這個我也沒什么好說的,刑警們都是用鮮血在拼的。但法醫(yī)的作用很大,培養(yǎng)周期時間又太長,一個法醫(yī)要上五年的大學。工作以后,又要五年才能拿到鑒定人資格。十年的時間才能培養(yǎng)出一個可以獨立辦案的法醫(yī)。很多地方都是青黃不接的,老法醫(yī)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很多法醫(yī)都是默默無聞的,從一個普通法醫(yī)做到退休。我認為能干到退休的法醫(yī)都是對這份職業(yè)充滿了熱愛。
采寫/新京報首席記者 劉瑋 實習生 葉彬彬 攝影/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